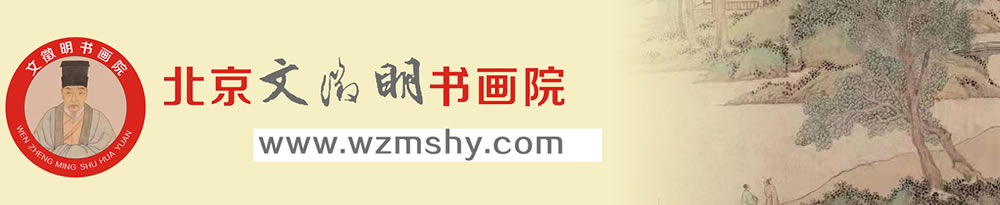盧素芬在2014年“衡山仰止——吳門畫派之文徵明”特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
日期:2022-03-23
作者:盧素芬 臺灣東吳大學
蘇州博物館于2012年正式啟動“明四家”系列學術展覽,首展為“石田大穰——吳門畫派之沈周”。而此次文徵明(1470-1559)特展則是一項更具規模的展覽,將海內外收藏的70余件精品匯集至文徵明的出生地,在展示空間上,增加了近一倍。參展的22家文博機構: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館、南京博物院、遼寧省博物館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、美國耶魯大學藝術館和檀香山藝術館等。此展不僅涵蓋了山水、花鳥、人物、枯木竹石等不同繪畫題材以及篆、隸、楷、草、行等不同書體作品,更是全面展示了文徵明書畫風格的主要歷程,規格之高、代表性之強,可謂千載難逢。
同時舉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,匯集來自海內外研究者的論文30余篇,中國美術學院范景中、上海博物館單國霖及凌利中等先生先后擔任學術主持。依風格流派、專題研究、個案研究三方面,對文徵明生平及其作品的真偽,文徵明的師承、仿古源流、延續傳播等問題進行探討,在題材上也囊括了山水、蘭竹、人物、書法等,完整呈現此吳門巨擘的全貌。此次研討會有不少新史料的發現和利用,使文徵明的形象變得越來越豐富,對于我們重新認識文徵明及其作品,提供了重要的依據,確是吳派研究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。
《雅債》的質疑
近年出版的《雅債─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》是此次研討會的討論焦點之一,因書中所形塑的文徵明,與中國學者們心目中的文徵明存在些許的落差。上海博物館的凌利中在〈文徵明家族的文脈及早期藝術活動〉一文中,開宗明義就說,柯律格(Craig Clunas)所寫的文徵明變得他都不認識了!《雅債》中所建構的文徵明是一個營營茍茍,甚至是有點精明與勢利的,幾乎挑戰了歷代學者心目中那位敦厚儒雅、胸懷坦蕩,主吳門畫壇五十余年的長者形象。由于柯律格顛覆了他所理解的文氏宗族歷代積淀的精神質量、也顛覆了他所理解的文氏家族特性,因而促成了這篇文氏家族的研究。
凌利中的研究乃是從文氏家族的歷史變遷進行溯源,梳理文徵明祖輩如文洪 (1426-1499),(包括家族姻親夏昶(1388-1470)、吳凱 (1387-1471)等)之前,早已形成并奠定的宗族品格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展很難得地由上博借來一件書法作品《詠文信公事四首》,內容為詠南宋文天祥(1236-1283)事跡,正可為此文作最佳的批注。文徵明的先祖文寶與文天祥是一脈同譜,潛意識里,文天祥對文徵明道德的規范應當有一定的影響。過去對文徵明書畫淵源的研究,往往將其父輩,如文林 (1445-1499) 等,作為家族成員從事文藝、拓展人脈的引導者與奠基者,這篇論文則是更有系統的追溯整個文氏家族,對文徵明的硏就很有貢獻。
與柯律格看法之分岐的,還有中央美院的杜鵑,在其〈王世貞與文徵明─書畫交游與鑒藏研究〉一文中,也對柯律格提出反駁。柯律格認為王世貞(1526-1590)的《文先生傳》與一般死后立即發布的訃文內容并無太大不同,而且顯然特別參考了黃佐的墓志銘,但對于銘文中表明文徵明性格的三則軼事則做了一些更動,最終很大程度地改變了它們原來的含義。然而,杜鵑認為柯律格的誤解,在于他可能忽視了王世貞的史學家身份,而且對中國古代文人寫作的語境(context)的理解也有偏差。杜鵑又說,柯律格所忽視的是王世貞所作《文先生傳》的資料來源,事實上,《文先生傳》是與先生之子彭及孫元發所共同撰次。因而,王世貞對文徵明的了解與認識,絕對是遠遠超出柯律格的想象,《雅債》一書中對《文先生傳》的質疑,是不能成立的。
吳派源流的探索
中國美院的任道斌以〈文徵明與元人書畫〉為題,點出文徵明是明代復興文人畫的重要人物。文徵明崇仰元代文人書畫家,對趙孟頫(1254-1322)尤為欽佩,可見這兩位大師之傳承關系的作品很多,此次參展的廣東省博物館藏品〈老子像〉即為一例(圖1)。任道斌的發言,從文獻與畫跡考察雙管齊下,既明了文徵明的藝術淵源,又揭示了文氏改變宮廷院體與浙派占藝壇主流的風氣、恢復與弘揚文人畫地位中的歷史作用。
接著,遠從美國而至,耶魯大學美術館江文葦(David Ake Sensabaugh)以其多年鉆研元代顧阿瑛「玉山雅集」的深厚基礎,發表〈探討吳趣:文徵明與元代文人遺風〉一文。文中提及14世紀中葉,是中國文人生活形式發展的重要時刻,繪畫變成了文人定義其生活的一種方式。15、16世紀早期,楊維禎(1296-1370)、顧阿瑛等人已然成為蘇州精英人士效仿的典范。文中不僅探討元代文人遺風在吳地的延續、更進一步說明文徵明是如何跳出傳統框架,并以繪畫形式重塑了吳地文人的生活。在此次展件中有《小楷鐵崖諸公花游倡和詩》(江西省博物館藏)(圖2)或《石湖 橫塘》圖頁(北京故宮藏),即可見證江氏所言。
來自世界各角落的學者,齊來追溯其源。對臺北故宮藏品極其熟稔的王耀庭,則以故宮所藏的〈江南春圖〉作為具體的實例,發表〈江南春圖研究〉。他運用圖像風格分析,更進一步補充了上述兩學者的論述。文中說明此作中「緑樹陰陰覆釣船」的圖式,在繪畫傳統中淵源有自,不僅可上溯至吳鎮(1280- 1354),〈漁父圖〉,甚至還可追溯至更早;而向下延伸,如其弟子陸治(1496-1576)的〈花溪漁隱〉也屬此種圖式。
最后,在探討文徵明藝術源流方面,還值得關注的研究成果,有中央美院的黃小峰〈古意的競爭:文徵明《湘君湘夫人圖》再讀〉,而這也是研討會中唯一論及其人物畫的文章。雖然這一篇在議程上是歸入「個案研究」的范疇,但所提出「古意的競爭」的理念,卻揭示了此吳門巨擘在承先啟后上的重大意義。黃小峰認為文氏通過參考傳世的《洛神賦圖》構造出二湘的形象,也借助于對唐宋繪畫文獻的理解來精心處理畫面的細節。這些努力都基于他對「古意」的認識和理解。正是由于當時圍繞「古意」產生的種種競爭,才促發了文徵明嘗試以新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態度。
蘭竹畫的熱烈討論
此次研討會所提交的論文,有關文徵明蘭竹畫多達三篇,因此也引起與會者熱烈的討論。首先,蘇州博物館的潘文協,以〈聊寫胸中逸氣-文徵明墨竹研究〉展開論述。文中先考察了文徵明日常閑居的竹下生活,例如此次展出的《人日詩畫》,幅中所繪其住處「停云館」之后,即有一片竹林。又征引了《甫田集》所載的「種竹詩」,說明文徵明是愛竹者。參展作品中,有一件來自吉林博物館的〈墨竹畫〉(圖3),頗得自然清新之妙。雖然我們無法得知這件作品所繪是否就是文徵明手植?但此為文徵明墨竹的特點和意趣的代表作,當是毋庸置疑。又說,文徵明所參與設計的「拙政園」,以竹命名就有兩處,都可見文人比德于竹之文化傳統。
中央美院邵彥接續,再深入探討〈文徵明竹石幽蘭圖及其相關問題〉。她認為文徵明是元代以來傳統筆法的最后代表,承繼趙孟頫“石如飛白木如籀,寫竹還于八法通”之觀念。傳稱文氏作品之竹石圖中,畫石多“破鋒鋪毫,輾軋拖動”,并不符合趙、文二人的用筆風格,均非真跡。還可推測作贗者中,文之弟子周天球(1514-1595)、其子文彭(1498-1573)等或皆有份。吳派的硏究在中國書畫的硏究史中,是最早被研究的議題之一,但至今仍存在許多懸而未決的真偽問題。
邵彥最后還以考古文化層受到干擾、文化盜洞來比喻偽作的問題所帶給藝術史家頗為龐大的工作。書畫鑒定專家王連起,此次研討會期而未至。但其所提交的論文綱要中,分析了文徵明書畫的真偽問題突出的原因,有助于我們了解文徵明硏究上困難的癥結所在。文中指出這是由以下幾點造成的:第一、當時文徵明書畫藝術成就高、影響大,其作品的價值誘惑力大,作偽者自然就會多。第二、學其畫的人多,除子弟學生外,還有很多人靠偽造其畫為生。第三、文氏書畫的風格鮮明而又幾乎五十年很少有大的面貌變化,作偽起來也相對容易。
雖然真偽之辨要專業始能為之,但賞析作品的優劣,只要誠心與作品展開對話即可。展覽中最長的手卷〈漪蘭竹石圖〉(遼寧博物館藏)(圖4),無疑是展場中最為觀者所聚焦的展件之一。在長達1210cm之長卷上,以蘭為主,補以竹石、荊棘、巨松。運筆瀟灑、墨法清潤,讀之有著行云流水般,無比的暢快。觀此原作,終于明白為何文徵明的墨蘭有「文蘭」之譽。遼寧省博物館的張鋒,所提出〈文徵明與“文蘭”—略論文徵明畫蘭的筆墨、結構與范式〉,便是對文徵明在蘭畫上的杰出表現,加以著墨。
風中的筆歌墨舞
前文所提及文徵明的蘭畫長卷,采取了趙子固(1199-1264)「聯幅滿卷」的方式來經營畫面,充分表現了手卷的形式之美。而折扇則是在卷、軸、冊三種固有傳統的裝裱形式外,加入一種既可兩面觀看、又便于攜帶的新形式,此一新形式的發展,更加彰顯了深厚書畫傳統具有的廣大的包容性。「舶來品」折扇,雖早在宋代就從日本經高麗傳入中國,但至明代才盛行,尤以蘇州文人最能將之發揮得淋漓盡致。浙江省博物館趙幼強所發表的〈小品大藝—試論文徵明對書畫折扇藝術創作的推動和影響〉與北京故宮李天垠〈扇中文氏風骨—故宮博物院藏文徵明畫扇研究〉,皆以文徵明的書畫扇為題。趙幼強認為明代進入書畫扇面興盛期,原因有:一是與當朝皇帝的喜好有關。二是與當時書畫界的積極響應有關。而文徵明書畫扇數量之多,質量之精,傳播之盛,似列為 “吳門四家” 之首(圖5)。李天垠緊接著介紹了北京故宮所藏文氏33件畫扇,其中涵蓋了江南山水、山水人物、高士人物、竹石、史地、花鳥各個題材,也囊括文氏不同時期的風格。李天垠的論文是首度刊布其院藏,為吳派研究增添許多新材料,頗值得學界關注。
蘭亭文化的延伸
文徵明是蘭亭書法和圖像創作的大家,以此為題的作品不僅見之于著錄、存世作品亦甚多(圖6)。誠如潘文協所說,「其齋號『悟言室』,乃出自《蘭亭序》中「悟言一室之內」句」,可見文徵明對歷史上蘭亭雅集之向往了!北京故宮的單國強〈文徵明《蘭亭修禊圖》與蘭亭文化〉一文中,分別就不同館藏的三件〈蘭亭修禊圖〉為例說明,例如北京故宮所藏的〈蘭亭修禊圖〉,其實是由〈蘭亭〉傳統圖式衍伸出來的「別號圖」,這件取之于友人別號「蘭亭」而繪制的蘭亭圖,豐富了「蘭亭文化」的內容。
清華大學的邱才楨又以不同的視野,來談〈曲水流觴的新時空:文徵明蘭亭圖中的圖式與德政指向〉。他說文徵明通過對新型時空關系的創建,以及對以往圖像中“羲之觀鵝”圖式的剔除,強化了“亭中書寫者”王羲之的權力。又以王羲之的《蘭亭序》取代雅集者的《蘭亭詩》,使眾人雅集變為王羲之的個人展演。在文氏的作品中,文圖的新型鏈接,顯示了其個人理念的強烈參與,暗示了文徵明的圖式動機與政教動機,建立藝術楷模與道德楷模的關聯。
吳派的園林畫
園林山水無疑是吳門畫派最具代表性的題材之一,與二三知己于園林、齋館中相敘,無疑是吳中文人最典型的生活縮影。除了上述由《蘭亭修禊圖》傳統圖式所衍伸出來的「別號圖」,還有兩篇論文也是討論園林畫。蘇州大學毛秋瑾,發表了〈文徵明與拙政園——關于兩種《拙政園詩畫冊》的研究〉。文徵明存世的詩作中有多首與拙政園主人王獻臣交往唱酬之作。書畫著錄中也記載有文徵明所繪《拙政園》多件作品。目前還能見到的兩種詩畫冊頁,一是收藏地不詳的《拙政園詩畫冊》三十一景(1533年),另一是大都會博物館所藏的八景冊頁(1551年)。學者們早已指出,《拙政園三十一景詩畫冊》至少有兩張在構圖上與沈周《東莊圖冊》相似,毛秋瑾認為三十一景的書法水平也有所欠缺,但繪畫風格屬于“細文”一路,兩種冊頁在園林畫史上都有重要意義。她還指出了高居翰等人的新著《不朽的林泉——中國古代園林繪畫》中對大都會博物館所藏八景冊頁的一處誤讀。
筆者也以〈文徵明《影翠軒》〉為題,將分藏于臺北故宮和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的三幅〈影翠軒〉,辨其真偽。再從圖史的互證,厘清畫中主人翁應是吳寬之侄吳奕(1472-1517),而非《吳派畫九十年展》圖錄說明所說「是文徵明的自我寫真」。在兩岸文化交流頻繁的今日,筆者首度將寧波天一閣博物館所藏的第三本〈影翠軒〉聯系起來,也更加證實并非該書如所言,故宮的兩本是「文徵明的一稿兩畫」。而經由拙文的考證,亦可推測出〈影翠軒圖〉,約繪制于1510年前后,大器晚成的文徵明,早期作品為數不多,這幅早期的園林畫也就彌足珍貴。臺北故宮是吳派研究的發祥地,1970年代所出版的《吳派畫九十年展》更是吳派研究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,期以拙文的修訂對前輩篳路藍縷之功,致以最高的敬意。
仕途的坎坷
來自山東博物館的鮑艷囡發表〈從仕途到歸隱-文徵明不同心境的見證〉,文中考釋兩件其館藏的書法冊頁。其中《文氏兩世翰墨》實是研究文氏的一手資料,此作為三次辭官原因可靠的史源根據,透過書跡呈現了文徵明這段在京時期不平凡的際遇。從這件比一般習見文氏書作,更為潦草的手跡中,看到「因跌傷右臂不能舉動」、「目昏足蹇趨走不前」等辭官理由,三乞始獲準還鄉,其坎坷的心路歷程歷歷在目。雖然之前已對文徵明九次鄉試皆不售的生平事跡,耳熟能詳。對他在京時屈為九品待詔、面對乏味應制文書與險惡官場的那段經歷,也不陌生。但心為書畫,透過鮑艷囡所示衡山居士的手跡,此刻與大師更為貼近。
吳派的延續與傳播
仕途的坎坷在文徵明的人生道路上,其實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。文徵明結束京城的官宦生涯后,他的藝術生命才大大地開展,主宰吳門畫壇超過半世紀,桃李滿天下。中國國家博物館朱萬章發表〈文徵明弟子梁孜考〉,文中討論了一件近年廣東省博物館新購藏的一幅梁孜(1509-1573)山水畫,此文對衡山居士藝術的延續和傳播別具意義,因為梁孜這個名字是過去吳派研究比較陌生的。然而據朱博士的研究,梁孜不僅曾游于文徵明門下,得到文徵明的贊賞,并和當時吳中地區的重要文人一直保持著非常友好的關系。梁孜一生主要的藝術活動,是以“吳中”與“都門”為代表的當時主流文化區域。后來,他返回故鄉廣東之時,還攜帶了江南之牡丹,梁孜在故里對牡丹悉心培植,因而枝繁葉茂,鮮花盛開。而由于嶺南向無牡丹,所以梁孜對所種之花不服其習性,因而以花粉過敏染疾,后來幾經延醫,終無藥可治。雖然這段學成歸鄉的故事,最終以悲劇收場,但梁氏對牡丹的移植,也對日后嶺南地區的繪畫增加了新的題材。
朱萬章所論是關于文氏的弟子,而上海博物館黃朋則以研究其后代子孫為議題,在其〈嘉靖間文人鬻古牟利現象的興起—以文彭為例〉一文中舉出,文彭曾給項元汴(1525 -1590)的尺牘上,寫著:「四體千文佳甚,若分作四本,每本可值十兩,其文賦因止欠佳,故行筆澀滯耳!雖非佳品,然亦可刻者也。」建議項元汴該如何做生意,將原本一套的作品拆件分售好牟利賺錢。聽黃朋說到此,筆者不禁令人想起終其終生孜孜不倦的文徵明,每日清晨起來,必先練習千字文。而其長子文彭日日耳濡目染,見過無數的文徵明千字文手跡,沒想到千字文也成了他開發文創商品的靈感了。雖然黃朋所述確實反映了明代社會的變遷下,書畫市場的活躍與文人的改變。然而文氏后代在書畫上,有杰出表現的仍不乏其人,不容忽視。
文氏兄弟改名的原因?
蘭竹畫的贗品問題,引起熱烈討論,而書法作品的真偽問題同樣存在。蘇州博物館的李軍發表了〈再論文徵明小楷《落花詩》〉,針對過云樓、虛白齋、棐幾軒不同版本《落花詩》加以申論。其研究也再度引發出文徵明早年名字的探討,到底是文「壁」。還是文「璧」?過去,一般學界都普遍認為文徵明兄弟都以星宿為名,兄文奎、弟文室,故應是文「壁」,而非「璧」。至于,印文又為何寫成「璧」?以往也有研究認為在虛白齋所藏的《落花詩》中,文「壁」款為真,而文「璧」印,可能是后人偽造添加。總之,其撲朔迷離、錯綜復雜的關系,誠如學術主持范景中先生在開場時,就以幽默的口吻說,藝術史研究者的工作就像福爾摩斯偵探離奇的懸案一樣。然而,李軍不僅藉其《落花詩》的個案研究,再度引發對此兩字的討論,他又提出的問題是,文徵明改名的原因是為了甚么?為什么文徵明兄弟都要改名?頗值得學界再關注。
還會重現人間嗎?
我們所能見到的存世作品,其實只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偶然保存下來的片段記憶。遼寧省博物館郭丹發表的〈《佚目》內外的文徵明書畫〉非常值得關注,文中提及文徵明作品是在乾隆年間大量進入清宮,最多時達209件,而溥儀以賞賜之外盜出宮的文徵明書畫精品達43件。目前《佚目》所見流傳于世的有20件,例如展件中的遼博的〈滸溪草堂圖卷〉(圖7)、北京故宮的〈洛原草堂圖〉皆屬之。在郭丹所提及的作品中,臺灣讀者較為熟悉的,當是蘭千山館于寄存臺北故宮的〈宋高宗賜岳飛批札〉,這也是曾載入《佚目》的清宮舊藏。不過,下落不明者仍有23件,誰也不知道是否還會重現人間?我們仍寄予期待。
藤友們!后會有期了!
「衡山仰止」著實是一個全方位的展覽,除了匯聚來自四面八方的研究者共聚一堂進行交流,在教育推廣也多所著墨。館方利用特展的資源,設計了40款文創商品。文創商品在教育推廣上與導覽手冊同具功能,甚至更能深入生活,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,限量發行的文徵明手植紫藤的種子。這株就在蘇博館內的「活國寶」,已歷經四五百年的風雨滄桑(圖8),此回與會者帶著它的種子,傳播到世界各地。我和朋友們相約,往后email聯系時,當附上各自的紫藤近照,我們除了是衡山居士的「粉絲」,也成「藤友」了!(展期2013年11月10日至2014年2月16日,同期在蘇州碑刻博物館尚有“停云留翰——文徵明之碑刻拓片特展”配合展出)